Published on 07-06-2021
《再生騎士》(The Rider),2017,趙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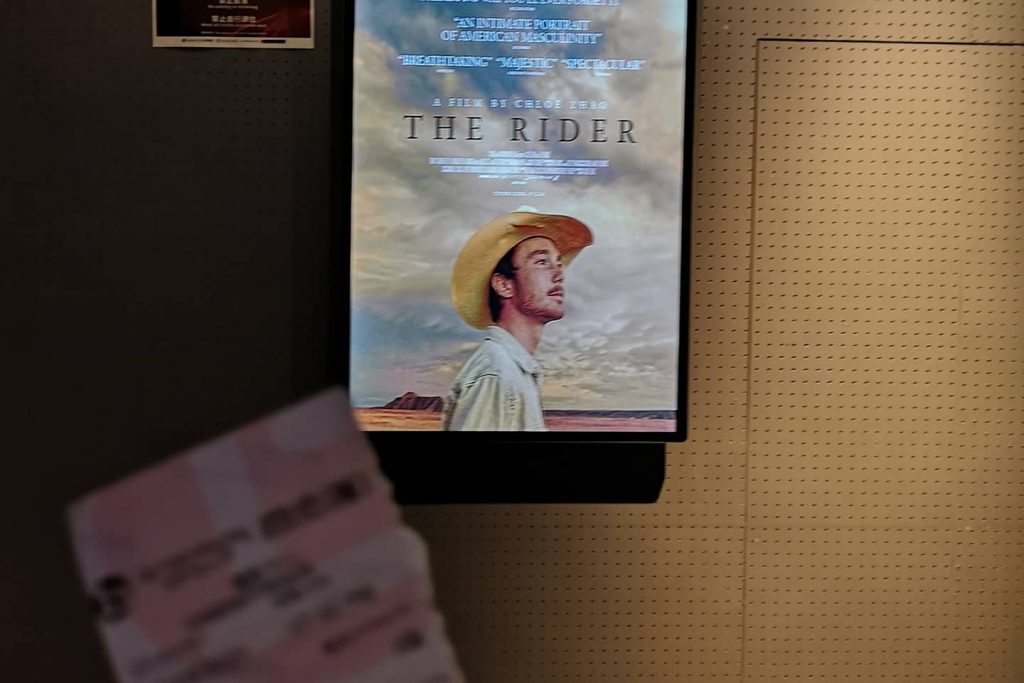
在家中執拾舊物,從書櫃中深處拈來一本五十七期的《字花》,隨書刊附送雨傘運動訪問集《傘沿》。年月過去,紙頁沒有一絲泛黃。細細翻閱,一則中學生徵文投稿《鳥語》讀來雲淡風輕,饒有餘韻:

「我累極了。就在我快要睡著時,我聽到鳥的叫聲。我好奇地從窗外望出去。樓下的街市,無論早上有多繁榮,晚上也得靜下來。街上只有幾輛車駛過,也暫時沒聽到任何人醉酒鬧事。在萬家燈火下,那隻鳥無跡可尋。
看!就算母親真的是一隻鳥,我看不見她,她看不見我。」
「我」的母親工作辛勞至死,剩下「我」和爺爺住在深水埗劏房。文中以鳥貫穿全文,以死人化鳥的意象寄託對母親的思念,亦只有死亡才能化鳥獲得自由,逃出城市的籠牢。我城璀璨的背後,中學生哀而不傷地娓娓道來。教我好奇,這般有才華的少女,五六年後還有好好寫作、好好生活,當一隻自由的小鳥嗎?
最近戲院重映了趙婷的《再生騎士》,這位拒絕謊言的導演的電影還能在香港觀看。人無疑是社會齒輪下的一顆螺絲,但我相信,唯有理想是生命的圖騰,唯有信仰能帶領我們逃脫現實的五指山。儘管生活有許多苦難,我們只能不斷適應,順藤摸瓜地尋找一個相對幸福的模式。若未經歷過悲傷,怎會知道什麼是幸福呢?
美國中西部南達科他州的草原鬱鬱蔥蔥。黎明未至,蟬聲噪動,一聲接一聲,大地更蒼茫幽靜。馬兒古斯靜候主人布雷迪,這個重傷初癒的競技牛仔輕輕躍上馬背,從漫步到奔馳,從夜深走到日出,既自由又無力。這個詩意時間把電影推向第一個高潮。翌日,被賣掉的古斯登上貨車,從此離開布雷迪的生命。
《再生騎士》是一部寫實而詩意的作品,場景回到印地安人蘇族中拉科他族的聚居地。現代城市光怪陸離地高速發展,但這片土地彷彿凝住在古老的某一瞬間。養馬維生,騎馬為樂,競技場上更是熱血沸騰。
傳統西部片以槍林彈雨的商業手法,刻劃老牛仔的俠義情懷;《再生騎士》卻以簡潔明淨的鏡頭,追索生命的本質: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?蒼茫大地上的奔馳,人與馬的親密互動,既溫馨又浪漫。主角布雷迪的故事從失去開始,慢慢爬梳出一個追尋與探索的成長旅程。
布雷迪是有名的競技牛仔明星。一場墮馬意外影響布雷迪的身體機能,不時癲癇發作令他無法好好騎馬,更無法再返回競技場上,只能在超市做打雜,宛如喪失自我。「如果造物主創造萬物,賦予萬物存在的意義和本質。馬不能在草原上奔馳就必須死亡,那麼人呢?人可以改變自己繼續生活,不是很不公平嗎?」
本質與存在的哲學命題,演變成布雷迪對人生意義的詰問。”I would truly risk my life to keep doing what I love.” 不惜一切追求真正喜愛的事物,但Lane Scott在醫院癱瘓的身影,敲響了布雷迪生命的警鐘。電影中最殘酷的象徵,莫過於賣馬和殺馬,印證競技生涯的終結。
電影於2017年上映。一次分享會上,主角布雷迪一身牛仔服飾坐在台上。誰想到影片中的故事是他的真人真事?布雷迪演活了自己,片中演員也是當地素人。趙婷憶述,她某天在酒吧喝酒,偶然看到布雷迪安撫馬匹的身影,她想到:如果他能掀動馬匹的情緒,或許他也能感染觀眾,或許他能演出。
布雷迪頭上如火車軌的傷疤是真的,不能再當競技明星也是真的。電影中的那份自然,不少也是日常生活裡的小故事。片末執拗的他一度衝動要返回比賽場上,但場外父親和妹妹守候的身影,教他不忍。最後默默走回家人的身邊,黃昏下駕車回家。
我們認識到自己的不能,只能發掘生命的不同可能。而成長就是失去、探索再發現的蛻變過程。
布雷迪笑言:“60% based on my true story and 40% completely fiction.” 趙婷回應:“we need the facts but also need poetry.” 電影在真實與虛構遊走,有觀眾不禁推敲,趙婷有否受到巴贊或盧馬等法國新浪潮導演的影響——電影之於世界猶如一扇窗,創作者應努力營造一個看不見鏡頭干預的世界,而非像高達般強調電影的虛假。趙婷笑一笑,政治學出身、半途出家的她坦言:王家衛令我喜歡電影,影響我的創作風格的則是泰倫斯·馬利克!
一切就是這麼純粹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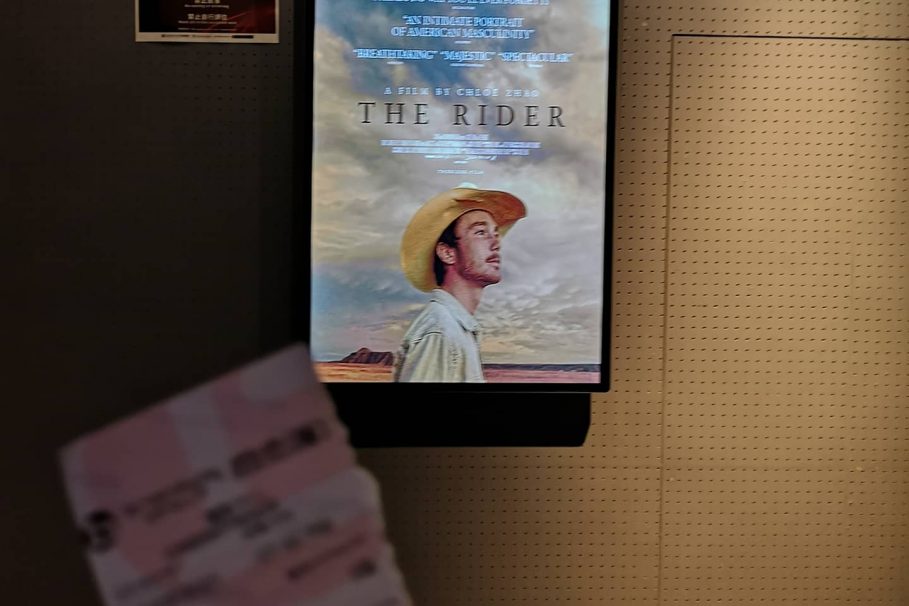
 吳雨霏《人非草木》
吳雨霏《人非草木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