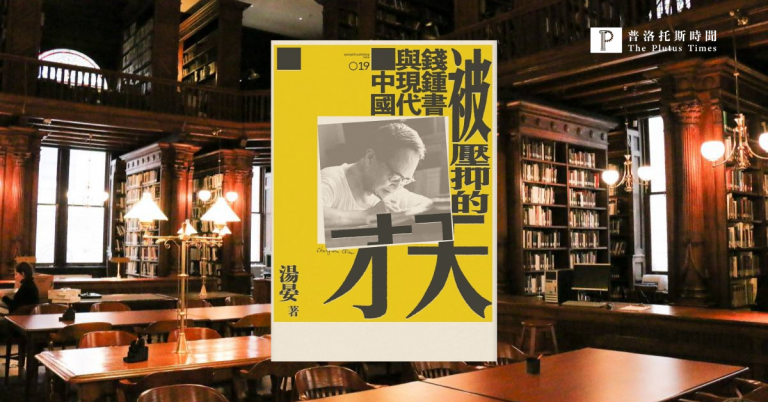Published on 06-09-2020
★錢鍾書一百一十歲冥誕紀念新版
★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楊佳嫻.推薦序
楊絳致湯晏函:「您的《錢鍾書傳》快要出版了,我向您賀喜。您孜孜矻矻為他寫傳,不採用無根據的傳聞,不憑『想當然』的推理來斷定過去,力求歷史的真實;遇到不確切的事,不憚其煩地老遠一次次來信問我,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。我很佩服您這種精神。」
錢鍾書是一個現象級人物,美譽環繞:「民國第一才子」、「文化崑崙」、「學貫中西」;余英時稱他是「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」,清華師友都說他是「天才」。但這樣一個天才,曾有長達三十年時間,在兩岸湮沒無聞,直到八〇年代臨老才獲得應有重視。時代為何辜負了他?本書作者湯晏先生,秉持史家作傳嚴謹精神,以簡潔流暢之筆,勾勒錢鍾書一生命運流轉,前半部敘述其秀異天賦的展現,後半部講他在極權統治之下,天賦異稟卻無法發揮,淪為「被壓抑的天才」。
錢鍾書出生於一九一〇年江蘇無錫書香世家。一年多後,溥儀退位,中國兩千年帝制瓦解,顛簸走上成為現代國家的荊棘之路。降生在此重大歷史節點的錢鍾書,其人生轉折乃至著述軌跡,均與現代中國連番巨變緊繫相連。他大學讀清華外文系,後又遠赴英國留學、法國遊學,是因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已不能只懂傳統舊學,必須掌握西學。匆匆由巴黎返國,是因中日戰爭愈趨白熱,惟恐回不了家。寫《談藝錄》,是因珍珠港事變後上海落入日軍手裡,他被困淪陷區,欲紓憂患心思。《圍城》之後再無小說問世,是因一九四九年他選擇留在新中國,政治肅殺氣氛漸重,創作變得太危險。八〇年代掀起「錢鍾書熱」,則是因文革結束、思想解禁,他的舊作終得重新出版,迴響廣大。錢鍾書與現代中國,兩者命運實互為倒影。
本書原名《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》(2001),今年(2020)是錢鍾書一百一十歲冥誕,特推出增訂新版,以饗讀者。湯晏先生與錢鍾書夫婦長年書信往返,孜孜矻矻求證,這既是作者「不敢強不知以為知」(楊絳語)忠實態度的明據,也為後繼錢學研究者留下珍貴史料。
節錄:引言
我接觸錢鍾書的作品很早,回想我尚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的時候,某日放學回家,一位同學在我背囊中塞了一本書,打開一看,是錢鍾書寫的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。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,我囫圇吞棗,很快把它讀完。現在想起來,在當時我未必能夠懂得欣賞作者的睿智與文采。譬如,該書第一篇《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》就是一篇趣味雋永、意義深長的散文,借魔鬼夜訪錢氏和作者的一段對白,針砭時弊,隱寓嘲諷。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當推《讀〈伊索寓言〉》。也許是故事最迎合十幾歲大孩子的心理,我讀完後,還把全文抄錄在日記本裡,當時就認為作者才氣很高,文字俏皮。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,不久中共建立政權,國民黨退處臺灣,痛定思痛,想要找出失敗的原因(原因當然有千百種),最後得出一個結論:打敗國民黨的不僅僅是解放軍,知識份子也有份。這個結論正與19世紀英國學者布林沃–利頓(Edward Bulwer-Lytton, 1803—1873)的名言「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」(筆之力甚於劍)的說法不謀而合。因為國民黨有這樣的想法,所以,所有大陸的作家的作品在臺灣都被視為禁書,即使沈從文、錢鍾書等人毫無政治意味的著作亦不例外。從此在臺灣就看不到錢鍾書的作品了。
20世紀60年代中期,我去美國讀書,某日在紐約華埠友方書店看到一冊香港盜印的錢著《寫在人生邊上》,如見故人,很是高興,就買了下來。後來也陸續看到錢著的其他盜印本,如《人.獸.鬼》、《圍城》及《談藝錄》等,也一本一本地買來細讀,對錢鍾書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後來萬萬沒有想到,1979年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來美國訪問,我在紐約拜見了這位心儀已久的江南才子——錢鍾書先生。確切的時間為1979年4月23日下午2時,地點在哥倫比亞大學懇德堂(Kent Hall)四樓會議室。在夏志清先生為他安排的座談會上,我就坐在錢先生對面。這個座談會是很精彩的。錢先生講得一口流利而帶有英國腔的英語。事前沒有準備(也無從準備),可是他口才很好,有問必答,絕無冷場,妙語如珠。正如夏先生事後對人說:「錢鍾書表演了兩小時,滿堂熱烈鼓掌。」那年錢先生游美在東西兩岸學術界風靡一時。錢先生在《論文人》(收入《寫在人生邊上》)一文中說,「卡萊爾在《英雄崇拜論》裡說文人算得上英雄」,現在錢鍾書在我們心目中亦可作如是觀。
錢先生游美返大陸後,我們經常通信,我屢獲錢先生贈書,後來幾乎成了「錢迷」。那時我就有給他寫一本傳記的念頭,可是沒跟他提起,倒是我常常對朋友說,「我要為錢鍾書立傳」,這話當初說了好幾年,一直沒有動筆。光陰荏苒,二十年過去了。二十年來變化很大,錢鍾書從一個被冷落的人而變成「印第安人」(紅人)——一個熱門人物。他的作品如《圍城》等書不僅在大陸再版,且在臺灣出版,有關錢鍾書的書充斥坊間。過去二十年我讀遍了海內外所有有關錢鍾書的著作——從胡定邦及胡志德(Theodore Huters)的博士論文到大陸出版的張文江和孔慶茂的《錢鍾書傳》,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譯《管錐編》。我深深覺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論文太偏重於學術研究,而大陸出版的錢鍾書傳記也有些框框,有框框就有忌諱,就不能暢所欲言。胡適說得好:「傳記文學寫得好,必須能夠沒有忌諱,忌諱太多了,顧慮太多,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。」
錢鍾書晚年纏綿病榻,於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。故人凋零,不勝悲懷,更使我追念這位中國「當代第一博學鴻儒」。為了實踐二十年前許下的私願,我決心為錢先生寫一部「可靠的生動的傳記」。埃裡蓬(Didier Eribon)為福柯(Michel Foucault)作傳時一開頭就說:「寫福柯傳是不好寫的。」因福柯是一思想家,且著作等身。寫錢鍾書傳也一樣不好下筆。錢鍾書出版的書照西洋標準不算多,算不上「著作等身」,但他學貫中西,博古通今,思想敏銳,尤好諷世,所以有些話雖然他說得貌似平淡無奇,但卻發人深省。即使他寫的散文隨筆,也都是雋永意縱,涉筆成趣,差不多每一則都是好文章,且有至理存焉。所以錢鍾書傳不是那麼好寫的。
本文節錄:《被壓抑的天才:錢鍾書與現代中國》
- ISBN:9789869907262
- 出版社:春山出版
作者:湯晏
江蘇海門人,幼隨父母到臺灣。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,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。平時喜讀史書、人物傳記與文學作品。很喜歡《紅樓夢》。已退休,居紐約。著有《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》、《葉公超的兩個世界:從艾略特到杜勒斯》、《蔣廷黻與蔣介石》、《青年胡適,1891-1917》。